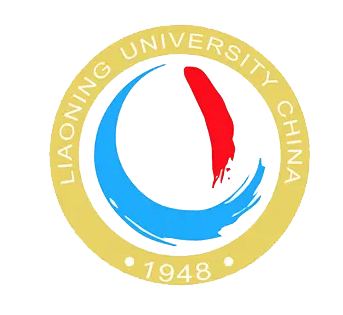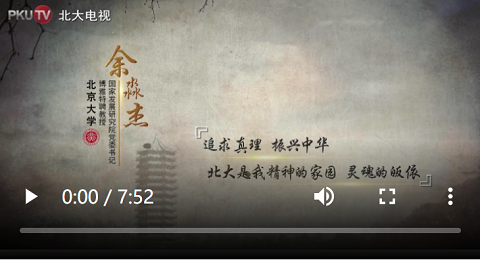印度正在遭遇制氧机等医疗器械的短缺。
此前印度已经从海外市场大量采购医院用消毒设施,病毒检测试剂等产品,它的本土医疗物资厂商远不足以满足疫情期间的需求。
制造能力的匮乏,是印度经济结构的长期问题。它以软件外包等服务产业融入世界经济,而缺乏制造业的根基。在疫情期间,这是一种致命的缺陷。
致命的短缺
印度新冠病毒感染人口以日均30万的检出量增长,医院的床位和制氧机等设备早已经无法应对涌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面对性命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需求,印度本土企业无能为力。鱼跃医疗等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填补了印度市场的缺口。在印度新一轮的疫情暴发期,鱼跃医疗接到了来自印度的上万台的制氧机订单。
鱼跃医疗董事长吴群告诉我,在制氧机领域,印度缺乏像样的本土企业。
制氧机的本土制造能力的匮乏,是一个突出的案例。除此之外,疫情期间印度进口了大量的消毒设施,病毒检验设备等,这显示出印度制造业长期以来的窘境。
中国和印度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开始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采取了关税减免、非关税壁垒取消等贸易自由化措施。但中国和印度在产业发展路径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看来,这是中国和印度经济今天差异巨大的原因之一。
“中国九十年代的改革,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逐步融入全球贸易一体化。加工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但是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很好的解决了第一桶金的问题,为未来的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余淼杰告诉我,“相反,印度九十年代看不起加工贸易,优先发展软件等服务业。这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白领的就业,没法实现大多数工人阶层的就业。这也造成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今天不能同日而语。”
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印度制造业增加值的7倍(1.61万亿美元/0.23万亿美元);十年后,尽管印度总理莫迪大力提倡印度制造,这一差距反而扩大至9.7倍(3.82万亿美元/0.39万亿美元)。在世界前五位经济体中,印度的制造业水平和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四国均有显著的差异。
在印度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一直比制造业更受到重视,软件外包等行业培养了一批高收入人群,也诞生了一些知名的公司如印孚瑟斯。
四年前,我参访了印度新德里、斋普尔等城市的科技企业。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当地蓬勃发展,也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但即便是软件企业,也会受到印度基础设施不足的困扰,在高档办公楼里的中国企业也要习惯不时的断电。
下一个制造业大国?
印度的制造业无力自主生产足够的医疗设备,它的公共卫生开支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用于建设公立医院和充实各个科室。
在印度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这是“不确定的荣耀”。“最近20年,印度的公共卫生开支在GDP的1%上下徘徊—很少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比这个数字更低。“他在2013年出版的书籍《不确定的荣耀》中表示,当时印度的人均GDP是孟加拉国的两倍,而孟加拉国的预期寿命却比印度长,儿童死亡率也比印度更低。
这种公共卫生开支畸低的状况近年来并没有得到改善。阿马蒂亚·森在《不确定的荣耀》里单列一章“印度的健康危机“,可谓一语成谶。
公共卫生开支欠缺之外,印度似乎也无法提供一种稳定的公共秩序。
在印度红粉之城斋普尔,疫情之前的游客能在同一条道路上看到人类几乎所有的陆地交通工具:两轮的自行车和摩托、三轮电力车、四轮汽车和马车,自由自在的牛穿街而过。斋普尔并非某个小城小镇,而是有着超过3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疫情之前它的经济活力充沛,但公共秩序的缺失同样显而易见。
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印度仍然放任数以百万计的人集聚参加大壶节,这令许多人暴露于新冠病毒环境。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里,公共治理能力的不足,在疫情期间是致命的。
在吴群看来,稳定的秩序是发展制造业必不可少的要素。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吴群认为印度体系没有中国完善,而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稳定政治体”,“中国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PK时赢过印度企业。”
印度成为下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可能性不高。余淼杰认为相对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印度已经没有相对优势,它的人口红利被种姓制度等问题所侵蚀。
印度的GDP总量先后超过了意大利、法国等一众国家,并于2019年超过了它殖民时代的宗主国英国,在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五。印度的发展曾激发了一种过于乐观的预期:高速增长会持续下去,并拉平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
不过,从最近五年的经济对比来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实际GDP差距是在扩大,而非缩小。余淼杰认为,中印经济规模的差距会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大。“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5倍左右,到十四五结束的时候可能会达到5.5倍。”
疫情在印度经济增长曲线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薄弱的制造业将是它长期的困扰。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海斌访谈